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剑桥校训: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
在一定意义上,当代中国正在按照西方的模式,特别是英美的两国的模式,打造自己的大中小学,因而很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机构的认识。
剑桥迄今未像其他一些大学那样屈从于一种压力,那就是强行将员工分成“专职研究人员”和“专职教员”两个种类。
英格兰的法律、经济、政治权力、家庭结构、阶级关系、个人性格等等,自有它们长期形成的特点,剑桥精神不仅是一面折射它们的镜子,也是一个塑造它们的模具。
虽然本书以剑桥为专题,但我所讲的同样适用于牛津。两校之间当然差别鲜明,却也酷肖得像是一家人,而且,与其说它俩是表姐妹,毋宁说是亲姐妹。……读者诸君仍有必要记住两校一家的事实。
避于一隅,与世隔绝,是剑桥的普遍现象,实际上也是它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在学术的等级制中,一个人的地位似乎不是用电话的多寡或地毯的厚薄来表示,而是用门的数目来衡量——看你究竟能在自己与外界之间设置多少重障碍。

剑桥无异于一粒小行星上的一颗微斑。奇怪的是,经过八百年的发展,这颗微斑变成了一个知识发现的重镇,据说在人类历史上堪称首屈一指。自然世界的法则定律千条万条,这里的科学家发现和制定的不在少数。我们不禁要问,这场探索“生命、宇宙、万物”之谜的伟大实验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剑桥科学、艺术、人文和社会学领域的创造力的泉源又在哪里?
人类天生具有创造潜能,无一例外。也就是说,他们会在好奇心、探究心和实验欲的驱动下,不懈地解决谜题,尝试新事物,探索周围的世界,发明改善生活的新方法。但是在大多数社会,人的创造力时常受到约束。国家、宗教、家庭通常会沆瀣一气,共同向个人施压,给他的创造力戴上枷锁。有时候,它们也会容忍甚至鼓励一些鸡毛蒜皮的创造活动,但是对于企图改变世界的大胆创造,它们一定视之为洪水猛兽。
教育体系本身,无论中小学层面还是大学层面,也经常充当创造性思维的绊脚石,所以爱因斯坦喟叹:“干扰我学习的唯一因素,就是我的教育。”教师们一味地依赖死记硬背,一味地崇尚既定真理和祖先智慧。学校里弥漫着对离经叛道者的强烈敌意。
虽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创造力喷发的时刻,但是每当我想到我的亲身体验,我就觉察到剑桥的与众不同。剑桥引发了一系列有人称之为“思维模式转换”的改变,从培根、牛顿、麦克斯韦,到克里克和沃森,很多剑桥人通过深度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在多数情况下,探索人类和自然的奥秘是一桩寂寞、孤立、不合情理、有点令人恐惧的事业,但是显然,它神秘地在剑桥找到了繁盛之地。
在探索文理科谜题的八百年长期奋斗中,高级研究人员在剑桥如鱼得水,学生也一样受到鼓励。无论中小学如何窒息了创造力,如何禁锢了“书蠹”和勤奋者,一旦进入剑桥,每一种创造潜能都会被激发出来。游戏、音乐、表演、诗歌、科学,无论你爱好和擅长什么,剑桥都会欢迎。
原创力是剑桥学术生活中最受重视的素质之一,也是剑桥长期以来选拔博士生的主要标准。探明新事物,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东西,找到解决老问题的新路子,开拓知识的新“矿层”,这就是剑桥的最高目标。
多种因素激发了剑桥人的创造性:
无论一个人想做什么,都会受到尊重
剑桥有一个基本推定:你的尝试也许暂时显得荒诞,却可能导致某种有价值的原创。这是有力的鞭策,也是一种愉快。宁可试试看,宁可从错误中学习,也不要禁止他们涉足坎坷之路。
职位和职称相对而言不分高低贵贱;研究与教学之间不存在尖锐的差别;更受重视的是口碑而不是正式职位。
在这里,最糟糕的名声是被人认为乏味,最受欢迎的事情是活泼而又顽皮的、探索性而非破坏性的谈话。
非凡的成就可能伴随着羞怯畏葸、糟糕的授课技巧、孩童似的天真、无可救药的自私。
剑桥人的共识是,一个人能取得非凡的成就,能成为一位牛顿、J. J. 汤姆森、保罗·狄拉克、弗雷德里克·桑格,却未必能轻易适应常规学术生活的琐碎。
一旦成为剑桥某学院的院士,就无需为进一步晋升而奋斗,除非是谋求院长交椅。
因此,一个人可以投入自己的几乎全副精力去改进教学,去研究难题,而不是去追求晋级和擢升。
剑桥创造力的另一个源泉,是专业之间或学科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某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知识范畴互相会合之日,便是产生最大的发明和发现之时。
剑桥的学院制促进了跨学科交流的广度。在我访问过的许多大学,人们一般只认识本学科和邻近学科的人。但是在剑桥诸学院,如果你是一名本科生,你会和来自种种不同学科的人交朋友。如果你有朝一日做了院士,你会和科学家、哲学家、古典学家或其他遥远学科的专家成为高桌上的邻座。
大学的核心精神就是好奇,盖因学术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力图答疑解惑。
解决了一个难题,你的头脑立刻又面临下一个难题。

剑桥的教育体系立足于两大思想源流。其一是古希腊思想,它的非凡之处是鼓励人们提出问题和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其二是中世纪英格兰的法律传统,它鼓励人们在为难题寻求可信答案时,进行对抗性的论辩。两个源流彼此交融,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求知行为,这种求知行为最终成为了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要素。
为了保障创造力的可持续喷发,剑桥设立了足够的界线和护栏——厚重的大门,排外的俱乐部,隔离的时间和空间,不同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休假期和研究期。然而剑桥并非一个严防死守的堡垒,流动不息的人口、络绎不绝的访客和学生、当今的互联网革命,使剑桥兼备了“渗漏性”。
学者的工作似乎经常是劳而无功,经常是一种漫长而烦琐的活动,驴推磨似的枯燥,而且,不是一无所获,就是重复前人的旧绩,偶有回报,恐怕也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著作、实验、论文进展滞缓;头发渐渐花白;朋友们在背后嘲笑你虚掷了生命。这时你很容易丧失希望,变得愤世嫉俗,转而退缩到某种立竿见影的工作之中,譬如去搞行政。
尽管如此,我们在许多伟大科学家的工作中仍可见到一种执著追求可信知识的精神,美国作家爱默生发现,这种精神也是整个英格兰民族的特性:“英格兰人对事实独具只眼,他们的逻辑是一种将盐送往汤、将锤送往钉、将桨送往船的逻辑,是一种厨师、木匠、化学家的逻辑,它紧跟大自然的次序,绝不为人的言辞所左右。”
只有盲目地保持惊异感、困惑感、好奇心——如爱因斯坦常说的那样,才能拂去踟蹰和犹疑。只有相信世界并非充满幻觉,或者充满印度教和佛教哲学家宣扬的“幻境”,才能拥有充分的理由,去坚持艰辛的求索,甚至不惜回归本学科的基层,从那里创造出全新的东西。
剑桥的年龄越来越老,但它设法做到了青春永驻;剑桥充满魔幻的气氛,但它从神秘中散发出现实的芬芳。对于一切与剑桥有关的人,它今天还在继续使他们愉悦、发笑、恼怒、激奋,而且有望世世代代继续下去。
以上节选自《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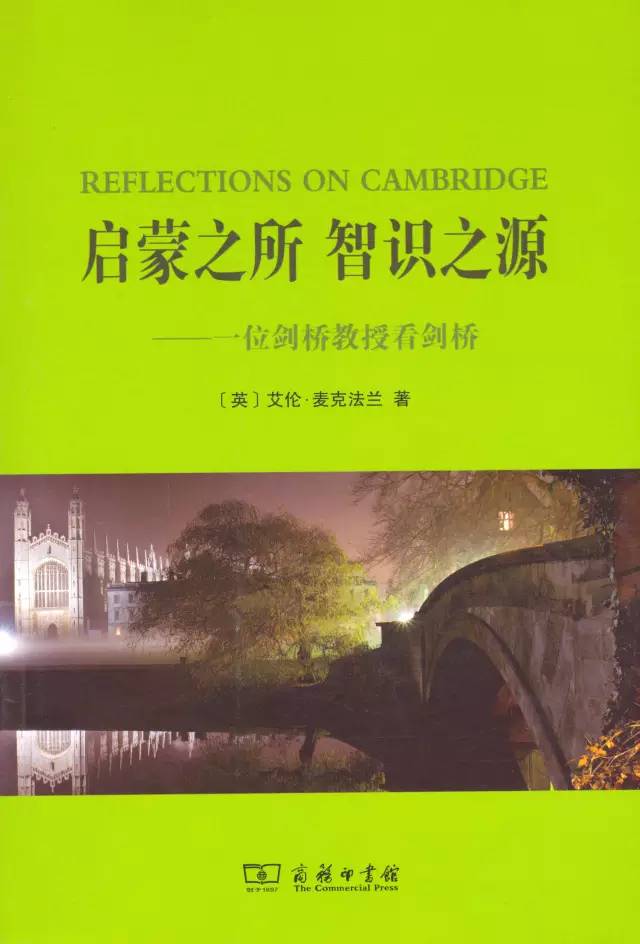
猜你喜欢:
剑桥校训: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
在一定意义上,当代中国正在按照西方的模式,特别是英美的两国的模式,打造自己的大中小学,因而很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机构的认识。
剑桥迄今未像其他一些大学那样屈从于一种压力,那就是强行将员工分成“专职研究人员”和“专职教员”两个种类。
英格兰的法律、经济、政治权力、家庭结构、阶级关系、个人性格等等,自有它们长期形成的特点,剑桥精神不仅是一面折射它们的镜子,也是一个塑造它们的模具。
虽然本书以剑桥为专题,但我所讲的同样适用于牛津。两校之间当然差别鲜明,却也酷肖得像是一家人,而且,与其说它俩是表姐妹,毋宁说是亲姐妹。……读者诸君仍有必要记住两校一家的事实。
避于一隅,与世隔绝,是剑桥的普遍现象,实际上也是它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在学术的等级制中,一个人的地位似乎不是用电话的多寡或地毯的厚薄来表示,而是用门的数目来衡量——看你究竟能在自己与外界之间设置多少重障碍。

剑桥无异于一粒小行星上的一颗微斑。奇怪的是,经过八百年的发展,这颗微斑变成了一个知识发现的重镇,据说在人类历史上堪称首屈一指。自然世界的法则定律千条万条,这里的科学家发现和制定的不在少数。我们不禁要问,这场探索“生命、宇宙、万物”之谜的伟大实验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剑桥科学、艺术、人文和社会学领域的创造力的泉源又在哪里?
人类天生具有创造潜能,无一例外。也就是说,他们会在好奇心、探究心和实验欲的驱动下,不懈地解决谜题,尝试新事物,探索周围的世界,发明改善生活的新方法。但是在大多数社会,人的创造力时常受到约束。国家、宗教、家庭通常会沆瀣一气,共同向个人施压,给他的创造力戴上枷锁。有时候,它们也会容忍甚至鼓励一些鸡毛蒜皮的创造活动,但是对于企图改变世界的大胆创造,它们一定视之为洪水猛兽。
教育体系本身,无论中小学层面还是大学层面,也经常充当创造性思维的绊脚石,所以爱因斯坦喟叹:“干扰我学习的唯一因素,就是我的教育。”教师们一味地依赖死记硬背,一味地崇尚既定真理和祖先智慧。学校里弥漫着对离经叛道者的强烈敌意。
虽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创造力喷发的时刻,但是每当我想到我的亲身体验,我就觉察到剑桥的与众不同。剑桥引发了一系列有人称之为“思维模式转换”的改变,从培根、牛顿、麦克斯韦,到克里克和沃森,很多剑桥人通过深度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在多数情况下,探索人类和自然的奥秘是一桩寂寞、孤立、不合情理、有点令人恐惧的事业,但是显然,它神秘地在剑桥找到了繁盛之地。
在探索文理科谜题的八百年长期奋斗中,高级研究人员在剑桥如鱼得水,学生也一样受到鼓励。无论中小学如何窒息了创造力,如何禁锢了“书蠹”和勤奋者,一旦进入剑桥,每一种创造潜能都会被激发出来。游戏、音乐、表演、诗歌、科学,无论你爱好和擅长什么,剑桥都会欢迎。
原创力是剑桥学术生活中最受重视的素质之一,也是剑桥长期以来选拔博士生的主要标准。探明新事物,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东西,找到解决老问题的新路子,开拓知识的新“矿层”,这就是剑桥的最高目标。
多种因素激发了剑桥人的创造性:
无论一个人想做什么,都会受到尊重
剑桥有一个基本推定:你的尝试也许暂时显得荒诞,却可能导致某种有价值的原创。这是有力的鞭策,也是一种愉快。宁可试试看,宁可从错误中学习,也不要禁止他们涉足坎坷之路。
职位和职称相对而言不分高低贵贱;研究与教学之间不存在尖锐的差别;更受重视的是口碑而不是正式职位。
在这里,最糟糕的名声是被人认为乏味,最受欢迎的事情是活泼而又顽皮的、探索性而非破坏性的谈话。
非凡的成就可能伴随着羞怯畏葸、糟糕的授课技巧、孩童似的天真、无可救药的自私。
剑桥人的共识是,一个人能取得非凡的成就,能成为一位牛顿、J. J. 汤姆森、保罗·狄拉克、弗雷德里克·桑格,却未必能轻易适应常规学术生活的琐碎。
一旦成为剑桥某学院的院士,就无需为进一步晋升而奋斗,除非是谋求院长交椅。
因此,一个人可以投入自己的几乎全副精力去改进教学,去研究难题,而不是去追求晋级和擢升。
剑桥创造力的另一个源泉,是专业之间或学科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某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知识范畴互相会合之日,便是产生最大的发明和发现之时。
剑桥的学院制促进了跨学科交流的广度。在我访问过的许多大学,人们一般只认识本学科和邻近学科的人。但是在剑桥诸学院,如果你是一名本科生,你会和来自种种不同学科的人交朋友。如果你有朝一日做了院士,你会和科学家、哲学家、古典学家或其他遥远学科的专家成为高桌上的邻座。
大学的核心精神就是好奇,盖因学术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力图答疑解惑。
解决了一个难题,你的头脑立刻又面临下一个难题。

剑桥的教育体系立足于两大思想源流。其一是古希腊思想,它的非凡之处是鼓励人们提出问题和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其二是中世纪英格兰的法律传统,它鼓励人们在为难题寻求可信答案时,进行对抗性的论辩。两个源流彼此交融,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求知行为,这种求知行为最终成为了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要素。
为了保障创造力的可持续喷发,剑桥设立了足够的界线和护栏——厚重的大门,排外的俱乐部,隔离的时间和空间,不同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休假期和研究期。然而剑桥并非一个严防死守的堡垒,流动不息的人口、络绎不绝的访客和学生、当今的互联网革命,使剑桥兼备了“渗漏性”。
学者的工作似乎经常是劳而无功,经常是一种漫长而烦琐的活动,驴推磨似的枯燥,而且,不是一无所获,就是重复前人的旧绩,偶有回报,恐怕也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著作、实验、论文进展滞缓;头发渐渐花白;朋友们在背后嘲笑你虚掷了生命。这时你很容易丧失希望,变得愤世嫉俗,转而退缩到某种立竿见影的工作之中,譬如去搞行政。
尽管如此,我们在许多伟大科学家的工作中仍可见到一种执著追求可信知识的精神,美国作家爱默生发现,这种精神也是整个英格兰民族的特性:“英格兰人对事实独具只眼,他们的逻辑是一种将盐送往汤、将锤送往钉、将桨送往船的逻辑,是一种厨师、木匠、化学家的逻辑,它紧跟大自然的次序,绝不为人的言辞所左右。”
只有盲目地保持惊异感、困惑感、好奇心——如爱因斯坦常说的那样,才能拂去踟蹰和犹疑。只有相信世界并非充满幻觉,或者充满印度教和佛教哲学家宣扬的“幻境”,才能拥有充分的理由,去坚持艰辛的求索,甚至不惜回归本学科的基层,从那里创造出全新的东西。
剑桥的年龄越来越老,但它设法做到了青春永驻;剑桥充满魔幻的气氛,但它从神秘中散发出现实的芬芳。对于一切与剑桥有关的人,它今天还在继续使他们愉悦、发笑、恼怒、激奋,而且有望世世代代继续下去。
以上节选自《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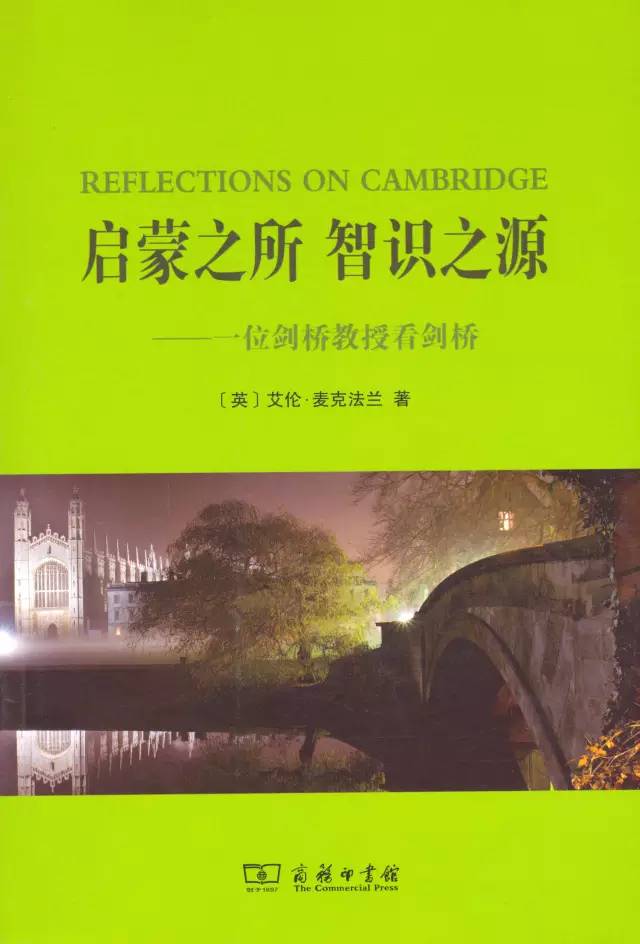
猜你喜欢: